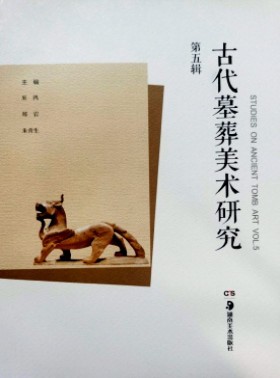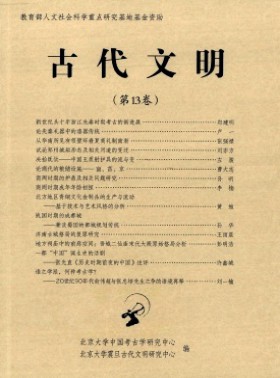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古代畫家的生態審美智慧,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郭熙是北宋時期著名的大畫家,也是畫學史上首屈一指的畫論家。徐復觀先生對其《林泉高致》的評價是:“并時,及此后的畫論雖多,然平實周到而深切,殆無能出郭氏范圍之外的。”[1]214郭熙的《林泉高致》一直為學界所關注,不過大家的學術興奮點多聚焦在郭熙畫學的哲學基礎、美學特征以及東西方構圖思想的比較等幾個方面,而沒有注意到《林泉高致》蘊含的豐富的生態審美智慧。事實上,郭熙的《林泉高致》作為中國古代山水畫論的集大成者,集中體現了古人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表達了古人對詩意棲居的理想追求,其中蘊含的生態審美智慧尤其值得我們探索。 一、“丘園養素”的繪畫功能論蘊含著濃厚的家園意識 家園意識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的重要美學范疇。海德格爾說,“在這里,‘家園’意指這樣一個空間,它賦予人一個處所,人惟有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運的本己要素中存在。這一空間乃由完好無損的大地所贈予。大地為民眾設置了他們的歷史空間。大地朗照著‘家園’。如此這般朗照著大地,乃是第一個‘家園’天使”[2]15,“返鄉就是返回到本源近旁”[2]24。海德格爾指出了家園意識的兩個特質:其一,“家園”是人自由的居所,是人與大地和諧共存的空間;其二,“家園”具有本源性。這就是說,“家園意識”雖然是當代的生態存在觀念,卻具有普遍意義,它深深地根植于人類的生存意識之中,并通過哲學、藝術等形式表達出來。郭熙的《林泉高致》作為中國古代山水畫論的最高成就,開篇便抒發了對“家園”的懷戀之情。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訓》開篇寫道:君子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隕鶴飛鳴,所常親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見也。直以太平盛日,君親之心兩隆,茍潔一身,出處節義斯系,豈仁人高蹈遠引,為離世絕俗之行,而必與箕穎埒素,黃綺同芳哉。白駒之詩,紫芝之詠,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泉之志,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之本意也。[3]632“丘園養素”,“丘園”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的生命空間,“素”即素心,即人的本真之心。在郭熙看來,“丘園養素”、“泉石嘯傲”、“漁樵隱逸”、“隕鶴飛鳴”這樣的人與自然和諧自由的生命空間才是人們“常樂”、“常適”、“常親”的家園,是人性的本源之境,而紛紛擾擾的俗世生活則有違人的本性,是“人情所常厭也”。但作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畫家,郭熙卻不能返回山水田園,不能做“離世絕俗”之行。家園之思猶在夢寐,“披圖細玩幽棲處,笑指青山是故鄉”[4]594,畫家之所以愛畫山水,實在是希望通過臥游山水撫慰對故園的懷戀,返回故鄉。需要指出的是,藝術家懷戀的不僅僅是人生的故園,更是那積淀在人類意識深層的人性生長起來的地方,那是人性得以生長的本源之境。在那里,人與自然擁有著本原性的和諧,人與自然建立了密切的情感聯系。在人性本源的居所,一切存在都與人的生存息息相關,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人們生命的一部分。人類文明的發展迫使人們離開故園,走進陌生的生存境域,但人們卻對回歸本源保持著永恒的沖動。在中國藝術中,自然就是人類精神的終極歸宿。藝術家進行創作不是因為自然界這樣那樣的美,而是為了構建精神的家園,滿足生命深處回家的渴望。 二、“飽游飫看”的審美觀照蘊含物我平等的生態智慧 在審美觀照方面,郭熙提出了“飽游飫看”的命題,這一命題內蘊著物我平等的生態智慧。郭熙指出:“欲奪其造化,則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飽游飫看。”[3]636他認為要創作出理想的藝術作品,就要遍游山川,閱盡天下美景,這樣胸中就自有丘壑,創作自然神妙。其一,對自然“以林泉之心臨之”的平等親和態度。以什么樣的態度去“看”,這是“飽游飫看”要面對的首要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西方畫學堅持的是“主客二分”原則,把自然視為與主體對立的客觀存在物。西方畫家總是從自身出發,觀照與自身相關的環境和世界,客體作為外在于人的存在,只是因其對人有用才有價值。在中國古代畫家那里,自然與人是同一的,山水自然也是有生命的存在,具有內在價值。畫家對山水進行觀照不是把山水視為與我無關的客體,而是視為與我血肉相連的關系存在。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對山水的觀照要“以林泉之心臨之”的命題。郭熙說:“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奢之目臨之則價低。”[3]632看山水要有“林泉之心”,就是說要有平等親和的態度。所以,在郭熙眼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凈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3]634。山水自然對人類而言不是冷漠的充滿敵意的他者,而是溫和的充滿親情的家園。相反,看山水如果“以驕奢之目臨之”,就會忽視山水的內在價值,喪失返回本真居所的家園感。其二,“三遠”的觀照方法內蘊著萬物平等的生態思想。在對自然的觀照方式上,西方畫學采取的是焦點透視的方式。透視原理是由15世紀意大利建筑師布魯涅列斯在研究建筑時用數學知識推算出來的。薩拉•柯耐爾說:“利用數學,他(布魯涅列斯)得出了線性透視的一條公式:各條線后退會聚于一點上,在這點上它們仿佛消失掉了。”[5]77通俗地講,焦點透視就是畫家站在固定的點上,依據近大遠小的法則,“把眼前立體形的遠近景物看作平面形移上畫面的方法”[6]100。焦點透視的基礎是科學主義,其以人為中心的觀照方式對于自然景物被遮蔽的部分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與西方畫學不同,中國畫學對自然的觀照則是采取散點透視的方法。郭熙的“三遠”說就是中國散點透視理論的代表。他說:“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后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3]639中國畫家不是站在一個固定的點上,以自我為中心觀察自然,而是抱著“林泉之心”,依據“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的原理從不同的角度對對象進行全面觀察。在中國畫家看來畫家要畫的不應該是畫家眼中的自然,而應該是本真的自然。運用透視法則觀察到的只是自然的表象,而無法把握自然真實的生命。宋代的沈括曾對采用透視畫法的大畫家李成極盡嘲諷之能事,認為李成“不知以大觀小之法”是在“仰畫飛檐”“掀屋角”[3]625。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沈括認為李成沒有把自然的本來面貌呈現出來。可見中國畫家不是不懂透視學,而是透視學不符合中國傳統的繪畫觀念。中國畫家要求山川溪谷每處風景都有呈現自我的同等機會,而透視法則人為地遮蔽了自然的本來面目,所以為中國畫家所不取。#p#分頁標題#e# 三、“易直子諒”的審美創造心理內蘊著古典的生態人文主義情懷 在西方畫家那里,繪畫是對外在世界的摹仿,因此西方畫家特別看重對藝術技巧的追求,認為只要掌握了繪畫的技巧,就可以創作出杰出的藝術品。早在古希臘時期,波里克勒特就曾依據畢達哥拉斯的學說,寫過一本叫做《法規》的著作,其中規定了事物各部分之間精確的比例對稱,用來指導美術創作。文藝復興時期,在科學發展的基礎上,西方藝術對技巧的研究達到了高峰,當時的許多藝術家,如阿爾伯蒂、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他們同時也都是科學家)都致力于比例的研究。德國畫家杜勒在談到威尼斯畫家雅各波研究比例的工作時說:“他讓我看到他按照比例規律來畫男女形象,我如果能夠把他所說的規律掌握住,我寧愿放棄看一個新王國的機會。”[7]161西方藝術的科學主義精神導致了人類理性的張揚,從而導致了一種激進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學。人的欲望的滿足成了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惟一值得考慮的東西。在中國古人那里,“藝即是道,道即是藝”[8]7。繪畫不僅是技術性的活動,更是道的體現。中國古人繪畫不像西方畫家那樣去創作逼肖自然的復制品,而是為了體悟道(自然本真)的存在。畫家體道的目的在于發揮自己的本性,從而盡物性,使萬物得到發育,藝術品只是畫家在體悟了自然之道后的自然的創造,所以古人把繪畫視為圣人之事。在中國古代畫家那里,一片山水就是一片心靈的風景,山水是自然與人的共同居所。中國古代畫家雖然也重視對自然外在的把握,但更注重自然本性的體悟,而這種體悟則是從畫家內心發出的。郭熙在談到畫家的創作時說:“人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悅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覺見于筆下。”[3]640郭熙對畫家創作時心理狀態的要求是要“胸中寬快,意思悅適”,也就是要有“易直子諒”之心。“易直子諒”語出《禮記•樂記》,所謂“易直子諒”之心就是平易、正直、慈愛、誠信的心態。一旦易直子諒之心生,那么人就能心情和樂,心里就能安定舒暢,性命就能長久,以至于合乎天道、通乎神明。通乎神明,就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本性,“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者則能盡物之性”[9]790,所以人情萬物自然就能得之于心,傳之于手,創作自然傳神。很明顯,這里所謂“易直子諒”之心就是“中和”之心。《禮記•中庸》對“中和”的解釋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9]773這種情感的中和狀態就是人性的本真狀態,“致中和”就可以天地各正其位,萬物發育成長。所以中國畫家看山水,不是把它看作可征服的對象,而是內蘊著深沉的生態人文關懷。中國畫家筆下的山水,不是外在于我的客體,而是可以盡己性,成物性,人與自然各正其位,共同繁榮的理想家園。 四、“可居可游”的審美目標體現了畫家對理想生態環境模式的追求 在前文我們談到,西方畫家追求的是對現實世界的逼真刻畫,張揚的是人的本質力量。中國古代畫家的審美目標不僅在于創作可供人們欣賞的藝術品,更是為了描繪一片人們可以容身其中的“可居可游”的山水。郭熙說:“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為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游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此佳處故也。”[3]632郭熙清楚地告訴人們,畫家筆下的山水不僅在于對山水的欣賞,更在于展現他的人居理想。郭熙筆下的山水,“大山堂堂為眾山之主”,在主山兩側布列客山,成環拱之勢。而山必有水,有林,有人居。至于客舍、村落的位置,郭熙說:“店舍依溪而不依水沖,依溪以近水,不依水沖以為害;或有依水沖者,水雖沖之必無水害處也。村落依陸不依山,依陸以便耕,不依山以為耕遠;或有依山者,山間必有可耕處也。”[3]642今天讀來,郭熙的畫論似乎不是在談繪畫,而是在規劃理想家園的建設。這個理想的家園,背靠高山,群山環拱,林木豐茂,村前有水,村邊有田。這樣的環境具有重要的生態學價值:村后的高山可以為人們擋住冬天的寒風;村前的溪水不僅可以在夏天為人們帶來涼爽的空氣,也可以用來灌溉農田,還可以為人們提供漁產品;蔭翳蔽日的林木不僅可以讓人們在冬夏都得到庇護,也為人們提供了薪柴;那近村的豐饒的農田,則為人們提供了足夠富足的糧食。這是一個有機的生態環境,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中,人與自然建立了密切的情感聯系。在這個環境中,一切存在都與人的生存息息相關,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可居可游”的生態環境不僅是人類物質上的家園,也是人類精神上的家園。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中國原始社會聚落的遺址一般都是背靠大山或丘陵,在山丘或平臺之上,處于山間盆地或丘陵山地地區,周圍有樹林,附近有水源,宜于農耕或日常生活。這樣的環境在遠古時代不僅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了物質保障,而且易于隱避和防守,為人類生存提供安全保障。而據俞孔堅對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及山頂洞人居住空間的考察,“這些古人類滿意的生態環境中,都包含有某些對群體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景觀結構,如圍合、走廊、豁口以及直接生境的可控性和邊緣特征等”[10]79。所以,我們不妨說我們遠古的祖先一直生活在類似的生態環境中。正是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中,人類文明才得以生長起來。百萬年來,人們已經適應了在這種環境下的生活,而對這種人居環境的需要也逐漸成為人性的一部分。所以古人對“可居可游”的理想生態環境的追求,不僅僅是“身居”的需要,更是“神居”的需要。“可居可游”的山水圖式成了古人回歸本源的理想途徑。正是在對“可居可游”的山水的創作與欣賞中,古人才得以接近生命的本源,從而獲得了與自然生命的共感與歡歌。 #p#分頁標題#e# 總的來說,中國古代畫論作為中國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蘊含著十分豐富的生態審美智慧。中國古代的繪畫藝術也正是在這些生態審美智慧的指導下,成為了中國古人心靈的棲居地。本文對郭熙《林泉高致》所蘊含的生態審美智慧的探討只是一種嘗試,相信進一步的研究會取得更多的成果。